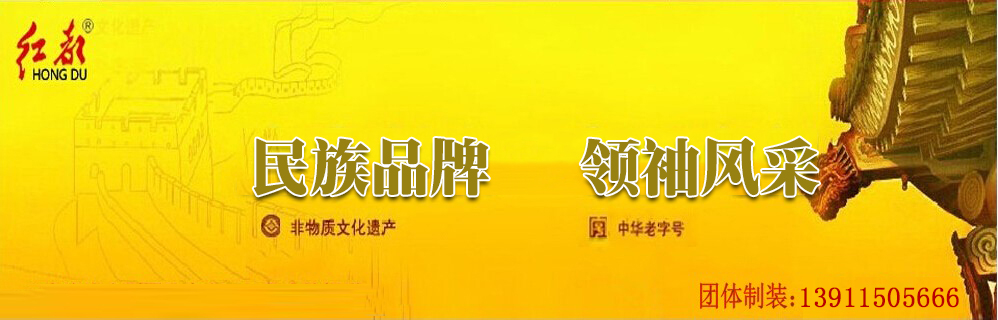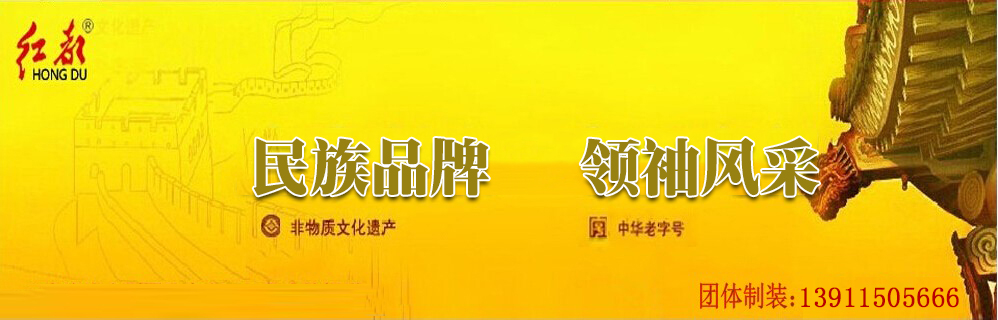話說科學(xué)院的研究員們,大多稱得上才高八斗、學(xué)富五車,但幾乎有個共同的毛病,對穿著打扮不怎么在意。這當然不是說他們的形象不好。今天回憶起龍瑞麟先生、陸維明先生一身布衣在講堂上為他們授課的情景,仍然有很多當年的研究生們?yōu)樗麄內(nèi)逖诺臍赓|(zhì)所折服,卻很少有人記得他們的大衣是什么牌子。以色列老祖母梅厄夫人,和以色列大學(xué)的女學(xué)生閑聊時曾說過:“我的縫紉技巧奇劣,但自十幾歲開始,我的衣服多數(shù)是自己做的,我相信別人給我評價,與我的服裝無關(guān)。”這大約便是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魅力。
至今筆者依然覺得這些穿著簡樸卻滿腹經(jīng)綸的科研人,是最有魅力的中國人呢。
這些知識分子不怎么講究衣著,還有一個原因便是他們在工作以外,普遍要承擔洗菜、做飯、帶孩子等種種家務(wù)勞動,也實在沒有條件如外國的教授們那樣打扮自己。正因為如此,在上世紀80年代的科學(xué)院宿舍,遇到一位西服革履的科研人員,是很容易讓人印象深刻的。
筆者記憶中便有這樣一位。
上世紀80年代初期,父親出國工作,筆者卻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。父親的同事們十分關(guān)心,大冬天里來看望的絡(luò)繹不絕。因為經(jīng)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地做項目,面對種種挑戰(zhàn),科研人員之間的友誼有的時候也和戰(zhàn)友很相似。
有一天又來了一位先生,身穿極精神的一身西服,看室內(nèi)狹窄,怕影響筆者養(yǎng)傷,他便站在沒有暖氣的廚房里和筆者的母親談話,了解情況。這位先生的西裝剪裁得體,上衣扣子有意沒有扣上,一手插在褲兜里,顯得十分瀟灑。對那個時代而言,穿西服的人少,便有穿者也多半不得要領(lǐng),這種瀟灑的形象似乎只應(yīng)該在外國電影或者國際會議的報道插圖上才會見到,故此令筆者記憶深刻。只是除此之外,覺得這位先生還有什么地方與眾不同,卻無法找出。
等到這位先生告辭離去,才豁然明白哪里不對勁兒,此時正是北京的寒冬,這位先生卻沒有穿外套,就這樣一身西服在寒風中泰然自若地飄然而去。要風度不要溫度的事兒,也傳到科學(xué)界了?
后來打聽,才知道這位先生原來是我國第一位赫哲族的大學(xué)生,數(shù)學(xué)家畢大川。
畢大川,黑龍江集賢人,出生于吉林大學(xué)數(shù)學(xué)系,擔任過中國科學(xué)院數(shù)學(xué)所助理研究員,系統(tǒng)所助理研究員、副研究員,航天工業(yè)部101所研究室主任,國家科委中國科學(xué)技術(shù)促進發(fā)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員等職務(wù),主要從事現(xiàn)代控制和軟科學(xué)的研究、組織工作,成績顯著,2007年當選國際宇航科學(xué)院院士。
當時對畢大川先生的事跡記憶不深,只記住了他的老家是黑龍江,筆者想,那里平時都是零下30度的氣溫,北京的冬天對畢先生來說恐怕只能算是“涼快”吧。
事后和數(shù)學(xué)所的老同志說起來,畢大川冬天只穿一件西服不怕冷,不是因為他出身赫哲族,東北人也怕冷的。他不怕冷因為他是運動員出身,另外,那時候他剛出國回來,除了西服,也沒有別的像樣的衣服。
這兩條都很有道理,根據(jù)記載,畢大川先生年輕的時候,喜歡體育運動,1959年參加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公路自行車比賽,還獲得過國家運動健將的稱號呢。他當時經(jīng)常參加國際交流活動,曾經(jīng)擔任過德國斯圖加特大學(xué)的客座教授。那一次他來看筆者,還有一個“任務(wù)”便是給同在國外的父親帶回家信和一些物品。
那個時候出國,國家是要出一部分置裝費的,西服是其中的必備品。對于當時簡樸的科研人員來說,一次出國置裝的結(jié)果,便是十幾年不需要再購買禮儀性的衣服了。
好像就是從見到畢大川先生以后,科學(xué)院里穿西服的便漸漸多起來,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像畢先生穿得那樣得體和瀟灑。后來才意識到,這似乎正是改革開放以后,科學(xué)院恢復(fù)和增加與國際科學(xué)界交往的一個特殊標志。畢先生他們,便是科學(xué)界這種國際化進程的先鋒。
筆者曾在網(wǎng)上談起過這件小事,不料卻被畢大川先生注意到了,專門派了一個助理與筆者聯(lián)系重溫這段舊事,并表示將來要是寫回憶錄,還可以把這段故事放進去。不料,這次寫作此文時,才發(fā)現(xiàn)畢先生已經(jīng)在2012年不幸作古了。只有那個北京的寒風中瀟灑自如的背影,仍讓人不能忘記。 |